好事多偶然。2018年11月14日晚,我和老戴与两位“国字头”报纸副刊的年轻编辑茶叙。一位编辑感叹道,纸媒(包括报纸副刊),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将来谁还看报纸呢?这对于毕生热爱报纸副刊的我,是个不小的触动。另一位编辑也说,新媒体的兴起是一个必然趋势,比如微信公众号。闻风而动。第二天上午,我便申办《谚云》公众号,下午即发出第一篇文章。
一、我们
白天上班,我带着一班人马打仗似地冲锋,工作节奏紧锣密鼓。晚上回家,写文章,做公号,我既是作者,又是责编、校对、排版、美编、终审、终校,一身多角儿,每天干到深夜,次日早晨发送推文。
做公号不是为了自弹自唱,孤芳自赏;而是为了将我们用心抒写的好的人和好的事,以及有益的知识理念和美好的价值观念,像春风一样吹拂,吹进更多人心间。为此,我还得做“产品营销”,拜托家人、朋友和同事们,帮忙转发微信朋友圈和各种群,尽可能扩大影响力。大约一个月后,一位年轻美女记者给我一个建议,说做公号要踩住时间节点,明天是冬至,您写一篇专稿,我们一齐帮着推送,保准能火。好主意!我通宵达旦草起一篇长文《说冬至》,于次日凌晨踩着冬至交节的点儿发出去,当日阅读量突破6000大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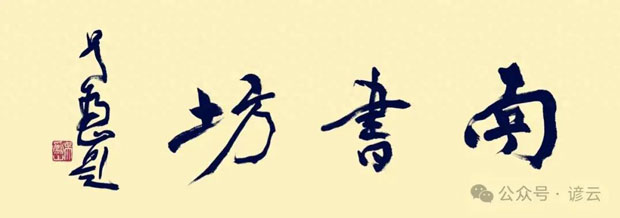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雕塑家、书法家吴为山先生为余题写书房名
先临渊羡鱼,再退而结网,是老戴一贯的行事风格。对于做公号,老戴先作壁上观,接着帮我校对稿子,静观两个月后,悄咪咪提交一篇《习书养气》,从此便开始源源不断供稿。老戴从不当着我的面写文章,每次都是我上班到单位之后,蓦地收到她从微信传来的稿子,附上一句“写得不好,请批评”,再配一个红脸冒汗的微表情。六年下来,老戴为《谚云》撰稿60余篇,其中仅2019年就写了23篇,可谓“铁肩担当”“独挑大梁”。只是到了2022年12月份“阳”了之后,老戴一直头晕至今,故后来写得少了些。
初办公号时,女儿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他默默关注《谚云》一个月后,突然打电话申请“加盟”。她说,同学们评价,爸爸妈妈两个人支撑一个副刊性质的纯文学公众号,一日推一文,做得这么好,太不容易啦;我也想做一个公众号,但一个人恐怕撑不起来,所以想加入咱家《谚云》,可以吗?——这还用说嘛!我笑呵呵说,“上阵父子兵”,平添一员骁将敢情好啊!没过几天,女儿即发来第一篇文章《牛津日记:别人家的孩子》。

女儿在牛津镇的餐馆里
古人云:“书疏尺牍,千里眉目。”本来是指古人书信往来,如同千里相约见面会话,日近日亲,相当于现在常说的“见字如面”。俗话也说:“千里万里,不如眼里。”我和老戴与女儿共同做公号、写文章、通电话的这两千多个日子里,对此感受颇深。父母与子女是骨肉血亲,亲字的繁体字写作“親”,由“亲”和“见”组成,正谓是“亲见亲见,不见不亲”。岂止不亲?西汉刘向《说苑·谈丛》有言:“亲疏则害,失众则败。”亲人之间日渐疏远疏离,不可避免造成误解隔阂,离心离德,甚而反目,往往会酿成灾祸。
近日女儿打电话说,为了给《谚云》供稿,每次写完文章,都要跟爸爸沟通好几遍,加之平时跟爸爸唠嗑得勤,所以我了解爸爸的“角度”有很多;跟妈妈就不一样了——妈妈向来嘴贵,交流相对要少,但是从《谚云》里频频读到妈妈的文章,让我有更多的“角度”观察妈妈,看到了往常许多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妈妈对生活观察细腻,妈妈心态平和温柔,妈妈的语言习惯也很不一样……我越是了解妈妈,就越能理解妈妈,就越想亲近妈妈,心里就会更爱妈妈。
颇有“哲学头脑”的女儿表示,她要是一直在爸爸妈妈身边,会比现在更出色。我笑着说,俗话说,“少不离家是废人,老不离家是贵人”,不离开父母哪能成人呢?女儿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是需要管教和约束的,生活在父母身边,能够受到良好约束,勤谨督促,严格管教,“自我内耗”——诸如胆怯,堕怠,侥幸,甩锅,自私自利,脑子想、手不动的患得患失等不良情绪,就会随时消化掉,心理问题比较少。她说,我经常跟爸爸沟通,在交流过程中,可以把自己大部分可能违背常情、隔阂亲情的负面情绪纠偏,打掉,回复清明向上的自我。女儿还说,我知道现在有不少青少年,包括留学生——特别是初高中就出去的小留学生,由于早期疏于跟父母沟通,又被充分“自由”地放养,缺失良好家教,除了要钱跟父母基本无交流,不少人缺乏挖掘身边最亲近人的美和善的能力,压根儿就不曾发现父母有爱的一面,父母成为孩子眼里“最熟悉的陌生人”,或熟视无睹,或充满怨恨,或水火不容,更有甚者对父母恨之入骨……这些人一旦走向社会,是很难融于社会的,他们会变成社会问题本身;其长期积累的负面情绪,也会成为阴霾一样笼罩家庭与社会的负能量。
我说,古人向来讲求“修齐治平”,讲究家风家教,就是先从自身与家庭出发,然后才走向社会,悲悯苍生,服务天下。因为所有的个人问题与家庭问题,终归都将成为或大或小或重或轻的社会问题。所以《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要达致这种美好的愿景,首先要从“亲其亲,子其子”做起,然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其“大同”理想才能由个人、家庭向社会发散。
《诗经·邶风·北风》有云:“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在创办《谚云》的六年中,正是我们一家人风雨兼程,团结一心,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批评,相互提高,共同影响,共同促进,共同升华,共同成长的美好历程。一位资深记者、我们的好友为真,持续关注《谚云》,对每篇文章都会写出精要点评,并真心点赞:“一家人,以亲聚,以文乐,不同一般的幸福呐!”
二、家园
微信公众号首页有一句广告词:
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
《谚云》公众号的品牌是什么?
我们做《谚云》公众号的初衷,缘于我心中根深蒂固的“副刊情结”。我工作之初,只当过一年半语文老师,其余36载职业生涯,都是做编辑记者,做过文学杂志、学术杂志、生活杂志、出版社的编辑,更做过多种报纸的副刊部、评论部、周末部、新闻部、专题部和子报的编辑、主编和副总编等。我在《红墨水·蓝墨水》一文中写过:“一位朋友讲过,所谓主编,就是主要的工作是编辑;所谓总编,就是总的来说是个编辑。仔细想来,这话讲得颇有理趣——编辑、主编、总编辑,无非都是用红墨水的。在做编辑的同时,我也是报纸的记者和评论员;业余时间,还喜欢写点杂文散文,以及有关民俗民谚的研究性文章。因而,我是左手红墨水,右手蓝墨水,既编辑剪裁他人的稿子,也经常为本报撰写稿件,时不时还会向其他报刊投稿。”
说白了,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业余作者”。

我在塞北故乡桑干河源头
老戴本职是人民警察,调京后在全国公安文联工作多年,但干的是联络部主任事务,每天写的是来往公文,作文章纯属于“业余爱好”。
女儿博士学的是化学专业,博士后搞得是合成生物化学方向研究的实验室“搬砖事业”,但她睡前爱看老子、孔子、《易经》、《诗经》、《史记》、《古文观止》和柏拉图、伏尔泰、维特根斯坦、莎士比亚、老托尔斯泰等古今中外文学哲学名家名著。女儿平时奔波于两个实验室之间,如果赶上滂沱大雨打不到车,便坐在一楼大厅沙发上,打开电脑码一篇文章,算是给《谚云》交作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美其名曰“被爸爸逼出来的”。她当然也是一个“业余作者”。
偶或愣神,回思历史,左孟庄屈司马诸葛曹陶李杜韩柳苏辛等历代文章巨擘,无一“专业作家”,即使困守穷庐啜粥度日的曹雪芹也只能算个“专业坐家”,均未获得甚么职称、奖项与特殊津贴之殊荣,不也都是“业余作家”吗?当然,历史上顶流的“业余作家”,与我等不入流的“业余作者”,相去岂止十万八千里哉!求同存异,殊途同归,只有“业余作”三个字相同,余者并不敢比拟攀附也。

老戴为写《通州城,好大的船》在运河沿岸以及西海子游览采风
然而,尽管我们的写作是“业余”的,但“作”文却不敢有一丝马虎。所谓作文之道,我一贯主张“文以畅道”,唯“作”而已矣。三个“业余作者”,六年来潜心耕耘《谚云》精神家园,深刻体会到微信公众号所特有的价值、功能与佳妙之处。我为它总结了“四个性”。
便捷性。公众号具有移动性、方便性以及低成本、多输出等特点,一部手机走天涯,让文章的发表与阅读,变得轻松、便利又简单。
及时性。谁的文章草就,都希望及时发表。且不说文学杂志之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等,如久旱之望云霓;即使是次日面世的报纸副刊,也未见得十天半月个把月就能发表出来。而我们的《谚云》公众号,今天做起今天就能发表,今夜做完明早就能看到,而且,还可以保障原汤原水原汁原味整个儿发表的完好性,故作为“业余作者”的我们,自由感、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豪迈感,油然而生。
互动性。文章一旦发表,就交给了读者,被指指戳戳,评头品足,横挑鼻子竖挑眼,在所难免。《谚云》不少文章刊出后,有私微,有私信,有留言,有电话,夸赞的,批评的,挑刺的,建议的,说啥的都有。俗话说:“褒贬是买主,喊喝是闲人。”又说:“受人教,武艺高。”批评受人指教,互动才能提高。当然,网络世界是个大林子,喊喝的鸟人也不少。
自主性。身为“业余作者”,上班已经充满刚性与规定性,业余时间尽可以“随心布施”,想写什么就写点什么吧。比如老戴写《线条》《苦豆豆》《文学与公文》《姐姐家的院子》等,女儿写《“植友”颂》《文与艺》《“隐形朋友”》《论斤卖的书》等,皆信手拈来,信马由缰,想到哪写到哪,不想写便作罢。“业余写作”状态,本来就是自觉自愿的,也是自主自动的,更是自由自在,发自内心深处的,诚如孟子所谓“求其放心而已”。“放心”者,本心也,良能良知也。

一家三口在深圳小吃店
修辞立诚著文章,正心诚意办《谚云》。三个“业余作者”经营着一片“自己的园地”,恰如《尚书·大禹谟》所谓“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不亦乐乎?不亦自足乎?
三、记录
然而,老戴总担心《谚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她分析道,受众的欣赏口味本来就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所以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时代,各种平台转换频次日益加快。二十多年前博客有多火,现在谁还写博客呢。还有,与持续性相对的是流行性。流行性一般具有新潮性、猎奇性、从众性、盲目性、舒适性、链接性、引领性、短暂性等特点,跟风儿就是一阵风儿,然后随风飘逝。这就是群体惯性与社会习气。公众号之后,又有抖音、短视频(包括播客、音频)等新媒体频现,特别是AI时代的来临,不知又要换什么“道”?我们的《谚云》还能走多远呢?
女儿却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她说,平台只是载体,内容才是王道,我们做好内容就是。女儿说,我近来睡前翻读古代的、西方的某些“宏大叙事”的历史典籍,均不乏遮蔽、捏造和篡改之处。而小人物的一生也是值得记录的,记录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普通人的故事经历和生活中一枝一叶的细节,将形成未来微观的也是具体的“历史背景”,往往会构成真实的“微观史学”。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记录自己的真情实感,留下我们所经所历所闻所见所思所感的真实文字。历代优秀的文人笔记,多被作为信史采用,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我们也要把《谚云》的文章,当作“微观史学”来书写。
俗话说:“一个巧皮匠,没张好鞋样;两个笨皮匠,有说有商量;三个臭皮匠,合成诸葛亮。”可见家庭与社会的群策力、向心力、凝聚力之重要性。对于老戴与女儿的意见或曰问题,我作如是想——
如今的读者观众尽在抖音、短视频中,整日里“沉浸式”地划拉着手机,究竟有多少人还在读书看文章呢?说不好,不好说,未作统计,不便妄测。不过,公众号与抖音、短视频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今后自然还会有新媒体平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不过,对于读者来说,信息过载目不暇给的疲惫感亦随之而来,故“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分流化与分群化,乃其必然选择。对于严肃文学写作来说,受众不会特别多,篇幅也不会特别小,并非三五分钟快闪式碎片化的抖音、短视频等,所能完全承载呈现的;再说,读者观众是会随时换口味的,看抖音、短视频与深阅读并不矛盾,有美有爱有用有见地的纯文学公众号也会“圈粉”,依然有其合理生存的空间;至少在新的可替代平台出现之前——即微信朋友圈冷清消失之前,我们的《谚云》仍将继续精耕细作办下去。
至于做内容,就要做出它的独特性来。
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乃至于写作的价值和意义,都是由自己来赋予的。曾看到几个“编辑家”做电视节目教导人们,再也不想看见写“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XX”之类的题目了,看见就要呕吐了!对于这种“题材决定论”者,我是素来不以为然的。没有什么题材不可以写。关键在于你要写好,写出你的“独一份”来。写好是本领,记录是使命。因而《谚云》多写我们熟悉的事,思考的事,挂心的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要比那些动辄拿“宏大叙事”“家国情怀”来说事的高调入云姿态高蹈者,更有人味儿,更富于生活气息。何况,“我情怀”与“家情怀”,本来就是“家国情怀”题中应有之义。《红楼梦》讲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练达”,自然也包含普通人生活中一个个有情趣有淬砺有人生况味的微镜头与小切面,“吟到恩仇心事涌”,“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都是好文章啊!
美在生活中,文学就在烟火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四、文章
做记录,做内容,首先要把文章做好。
何为文章?我曾在《文章论》(《〈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序》,2021年,东方出版社)中讲过:“汉代以来所称文章如《汉书·艺文志》所定义的‘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乃广义之文章;唐宋以前特别是魏晋时期以来,将诗词曲赋之类有韵之文与无韵之笔一同归入文章,算是‘中义’之文章吧;作为明清以后所称之文章(包含辞赋),已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文章之外延与内涵基本相同——亦即《现代汉语词典》所定义的‘篇幅不很长的单篇作品’,乃狭义之文章。《古文观止》属于狭义文章之范本。狭义文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章。”并以伟大的思想家、文章家鲁迅先生的杂文为例谈了我的想法:“在我看来,杂文倒也未必非要钻进什么‘高尚的文学楼台’,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章谱系,岂不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不忘初心、得其所哉吗?”

老戴和女儿在苏州阳澄湖畔
文章家与作家孰大孰小,孰重孰轻,每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我是向来看重文章这个概念的,故《谚云》里的作品都是以文章形式表现的。与文章相关的创作理念与审美体验,就像南朝梁代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所总结的体性、神思、情采、风骨、熔裁、养气、才略、程器等,都会给人以高古高深高级之启悟与美感。阅读审美是快乐的。写文章更是一种大快乐,可以瞬间调动所有的情绪、情感、知识、经验、修辞、语言、腹笥、经典、智慧、理念、思维、思辨等等,混沌与清明,穿越而飞飏!创作状态是庄严、神圣而喜乐的。诚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故好文章的吸引力与生命力,来源于作者的创造力与创新力;创造力与创新力,来源于作者的思想力与表达力;而思想力与表达力的核心,则在于作者的表现力与赋美力。因而我曾撰文讲,文章不仅要有意思,更要有意义;不仅要生动而深刻,还要看上去很美很靓,“虎豹无文,鞟同犬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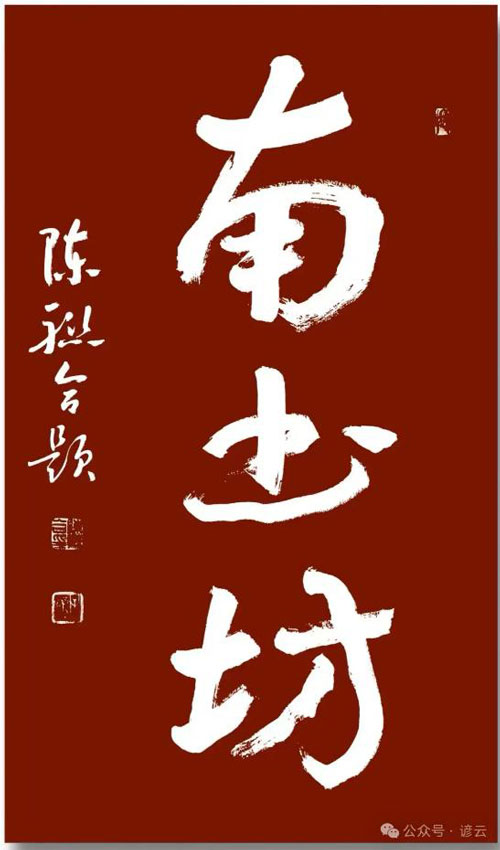
著名书法家陈联合先生为余题写书房名
不过,写文章如修行,自悟自道自发挥而已。即使一家人之间,可以相互点拨影响,但无法传授真经至道,故文章家向来“各自为阵”,独辟蹊径。历代文章钜子如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柳子厚、欧阳永叔的儿女们,亦并非文章里手。虽然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乃大文豪,但黄须儿曹彰却是“武豪”,何况曹操的儿子也不止于这几个;苏洵并儿子苏轼、苏辙均为大手笔,可是苏轼的儿子苏迈、苏迨、苏过也没啥大造就。这也正是文章之最神奇最宝贵的地方。艺术的真正高妙微妙之处,是难以“言传身教”的,诚如刘勰所谓“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文章大家尚且如此,而况“业余作者”如我等乎?
我们的《谚云》公众号已然走过六个春秋,固定订户近于两千,感谢诸君一路相伴走来!能够得到读者青眼,我们自然是很开心的。不过实质上,读者之多寡,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只要我们的文章有益于世道人心,裨益于社会家庭;只要身边的人以及社会上一小部分人,读了之后点头或沉思,微笑或留意,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们就已经很知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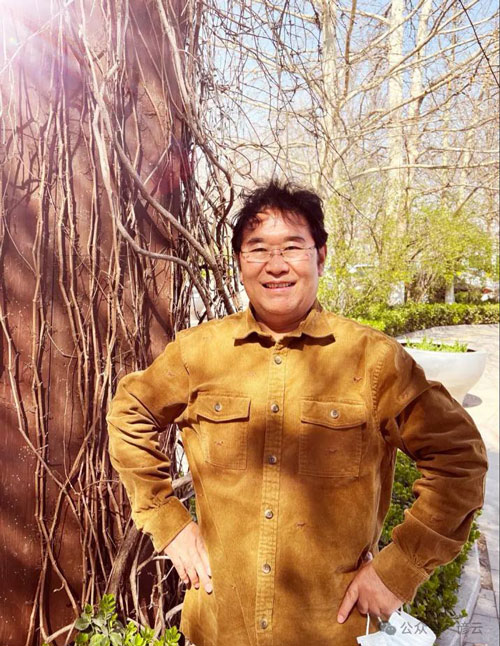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曾在阳泉市工作多年。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
京公安备11010102004047号